關注商業 * 傳遞價值 * 創造機遇
100年的這個季節,無數離鄉背井的年輕人在戰壕里迎來戰場上的第一個冬天。他們中許多人是世家子弟,6個月前,初上戰場的他們懷著騎士精神的浪漫想象,騎著高頭大馬,衣冠楚楚,整齊隊列的最前方是昂首演奏的軍樂隊。在他們踏上法德邊境馬恩河谷的那刻,不會想到僅僅6個星期后,死去同伴的尸體就堆到6英尺高。當秋天來臨,他們開始挖掘戰壕。隨著冬天的第一場雪降臨,他們帶著鋼盔困守在泥濘的壕溝里,不知道還要在膠著的西線廝守多久,不知道下一個圣誕節他們身在何處,不知道前方還有更多的死亡,更大的黑暗。
一戰爆發的第100個年頭過去,英國電影資料館籌備放映周期將長達四年的"電影中的一戰"循環影展的過程中,電影理論家大衛·湯姆森想起他在《視與聽》編輯部收到的一封讀者郵件,對方是28歲的美國青年,在看過根據雷馬克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《西線無戰事》后寫道:"我不得不慚愧地承認我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了解如此之少,它爆發于1914年,戰士們都帶著頭盔守在戰壕里,還有呢?"

還有呢?當我們試圖從電影中掃描那場戰爭,湯姆森不無失落地寫到,我們能看到的大部分關于一戰的電影,就像在戰爭第一年沖上戰場的世家青年們,被天真的騎士精神和英雄主義的血色浪漫遮擋著。在文藝的戰爭和戰爭的文藝之間,要穿過多少迷霧,才可能走近那段歷史的黑暗之心?
血色浪漫,以愛為名的誤會
想象的浪漫不可能療愈戰爭中真實的痛苦,也不可能挽回已然失去的,血色羅曼史成就的是好萊塢最早的消費文化,消費戰爭,消費死亡,消費人性。

美國官方在戰爭爆發后當即宣布中立的立場,美國軍隊沒有登陸歐洲,奔赴戰場的是好萊塢的第一代導演們,他們知道那片血與火的場域是一個富饒的素材庫。拍出《國家的誕生》《黨同伐異》的格里菲斯當然是個偉大的導演,他在一戰爆發不多久后親自到法國前線體驗了一下,并且在戰場上完成《世界之心》的一部分拍攝,這部由默片時期最賣座的女星莉莉安·吉許主演的"戰爭史詩大片"給好萊塢的同種類型片開了個非常糟糕的頭,它開創了"戰爭=亂世兒女情"這個無恥的等式。想象的浪漫不可能療愈戰爭中真實的痛苦,也不可能挽回已然失去的,血色羅曼史成就的是好萊塢最早的消費文化,消費戰爭,消費死亡,消費人性。《世界之心》是拉低格里菲斯職業生涯平均分的一部作品,那里面的戰爭是假的,愛情也是假的,只有一顆虛張聲勢的少女心罩著大時代的袍子。
 媒體管家上海軟聞:全國主流報紙紙媒媒體資源
媒體管家上海軟聞:全國主流報紙紙媒媒體資源  媒體管家上海軟聞:企業宣傳新品媒體邀約資源操作指南
媒體管家上海軟聞:企業宣傳新品媒體邀約資源操作指南  媒體管家上海軟聞:媒體邀約專訪全流程簡化指南
媒體管家上海軟聞:媒體邀約專訪全流程簡化指南  媒體管家上海軟聞媒體邀約:2025企業活動直播分發平臺選擇指南
媒體管家上海軟聞媒體邀約:2025企業活動直播分發平臺選擇指南  華北區新聞電視臺媒體資源:社會需求的瞭望塔
華北區新聞電視臺媒體資源:社會需求的瞭望塔  NEPCON ASIA 2025亞洲電子展10月28-30日深圳國際會展中心邀您共襄盛舉
NEPCON ASIA 2025亞洲電子展10月28-30日深圳國際會展中心邀您共襄盛舉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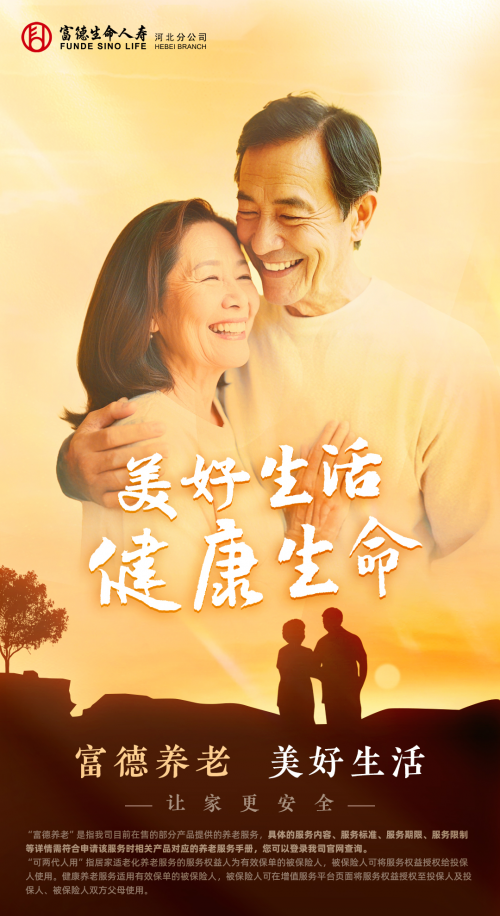 富德生命人壽河北分公司:守護居家養老心愿,共筑美好養老生活
富德生命人壽河北分公司:守護居家養老心愿,共筑美好養老生活  必康寵物醫療江蘇省第100臺DR裝機慶典成功舉行
必康寵物醫療江蘇省第100臺DR裝機慶典成功舉行  穩健醫療李建全談綠色手術室發展:綠色理念的前提一定是以人為本
穩健醫療李建全談綠色手術室發展:綠色理念的前提一定是以人為本  穩健醫療綠色發展之路:綠色手術室的創新實踐
穩健醫療綠色發展之路:綠色手術室的創新實踐  非遺醬油火爆出圈,13 道傳統工序怎樣創造時代新價值?
非遺醬油火爆出圈,13 道傳統工序怎樣創造時代新價值?  名創優品聯名“侏羅紀世界”產品火爆上新,電影主創團隊空降MINISO LAND逛店打卡
名創優品聯名“侏羅紀世界”產品火爆上新,電影主創團隊空降MINISO LAND逛店打卡